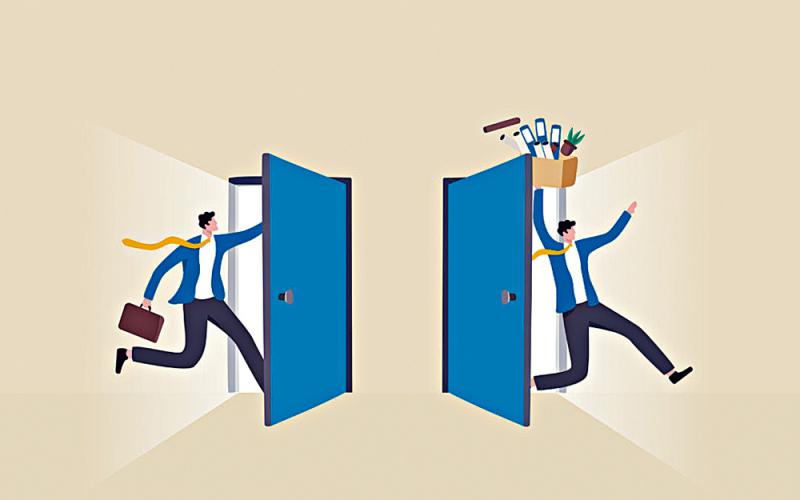
图: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令居家办公成为常态,也引发欧美一股辞职潮。\资料图片
几天前的傍晚,手机突然跳出一条语音留言,按下播放键,随即传来熟悉的声音,“老兄别来无恙啊,方便时咱们通个话。”这是我一位认识多年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朋友,算起来我们已大半年没有联系了。
看一下时间,此时正是英国早上九点多,通常他都非常繁忙,今天竟有如此雅兴,看来是比较清閒。我的猜测果然没错,通话之后才知道,他在几个月前已从金融城辞去了工作,目前待在家里成为自由职业者,这也意味着他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朝九晚五的上班了。更确切地讲,他自从去年初伦敦因疫情爆发封城后,便再没回过金融城办公室,一直处于遥距工作状态,如今他算是彻底解放了。用他的话说,经过一年多居家,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不想改变了。没想到,他也成了“大辞职”(the Great Resignation)浪潮中的一员。
说起“大辞职”,关注新闻的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这个由美国管理学教授安东尼.克鲁兹发明创造的词汇,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流行语,频繁地出现在西方各大媒体之上。按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克鲁兹显然借鉴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一词,虽然说两者在程度上不能相提并论,但都属于有着时代特点的社会现象。按调查机构的统计,这场大疫情之下的“大辞职”浪潮可谓来势迅猛,以美国为例,今年四月辞职人数接近四百万人,突破了二○○○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辞职人数节节攀升,九月份的数字已达四百四十万人,辞职率更是创纪录的接近百分之三,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以十万计的人辞去工作。
这股辞职潮也吹到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英国是深受影响的国家之一。与美国的情况类似,英国的餐饮、零售、医护和社工等行业也是辞职人数较多的领域,当然像医护、零售等工作原本就因为脱欧而导致人员短缺,如今更是雪上加霜。但英国有个尤为突出的趋势,即不少白领也成为辞职的主力军,就像我那位在金融城工作的朋友,他们辞职的原因也很接近:习惯了居家工作,不大愿意重返旧模式。英国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支持这种结论,比如Momentive的统计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表示,若雇主要求他们恢复全职工作并在办公室坐足至少八小时,就宁愿辞职。
除了希望居家办公而辞职者之外,其他人又是基于什么原因辞去工作呢?按照管理学专家马兹涅夫斯基的说法,参与“大辞职”的人大致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那些在“水深火热”与生存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比如某些行业的雇员经常要忍受低薪和加班加点等较差待遇,如今疫情令工作环境更加恶劣,他们觉得再做下去将不堪重负,必须辞职来改变这种局面。又或者人们经历了重大变故,包括自身在疫情中染疫或者目睹别人患病及死亡之后,开始反思和顿悟人生,他们因此改变生活态度,认为不能一切只围绕工作,希望辞职后能够寻找到生命的意义。
另一类则是在好与更好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比如英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持续发放保就业补贴计划(furlough scheme),让人不工作也有钱拿,加之环球“放水”的宽松政策,刺激股市和楼市齐升,受惠于此类财富效应,人们在考虑辞职时变得底气十足,认为保持现有状态才是他们想要的美好人生。还有那些高职位、高收入的经济条件优越的群体,他们在疫情期间饱受居家的困扰,因而辞去大都市繁忙的工作,转而回归原始乡间享受生活,就像英国热门电视节目《寻找理想小镇》(Escape to the Country)描述的那样,欣赏麋鹿在薄雾笼罩的田野上奔跑,啄木鸟在树丛中飞舞,静静倾听晨露从叶尖滴落的声音。
英国《每日电讯报》专栏描绘了英国人憧憬新生活可能的模样:有一栋又大又温馨的庄园,室内最好是石板地面,壁炉是那种复古田园风,须有一只憨态可掬的狗狗趴在前面吐着舌头。庄园离城市越远越好,附近还要有商店和可爱的小酒馆。在一个漫长的午后,全家人惬意地烤着火,吃着新出炉的点心,喝着下午茶;或者一起散步,孩子们一路兴奋地睁大眼睛,收集着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的甲虫、鸟巢和野花……听起来是不是很离地?但这就是许多人心中的世外桃源。
还需一提的是,在辞职潮中也有“躺平”族,如同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提到的“低欲望社会”的情形,他们以年轻人居多,既不想继续工作,也无欲无求。这些人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英国流行的尼特族(NEET)极为相像,就是不工作、不接受教育和培训(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终日无所事事,以一种近乎佛系的状态存在。
应当如何看待他们?《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艾肯沃尔德的话颇有启示:“大辞职”不是人们不想再工作,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意识到,在这个国家,美国梦已死。一同死去的,还有相信好好工作就能得到好的未来。英国又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