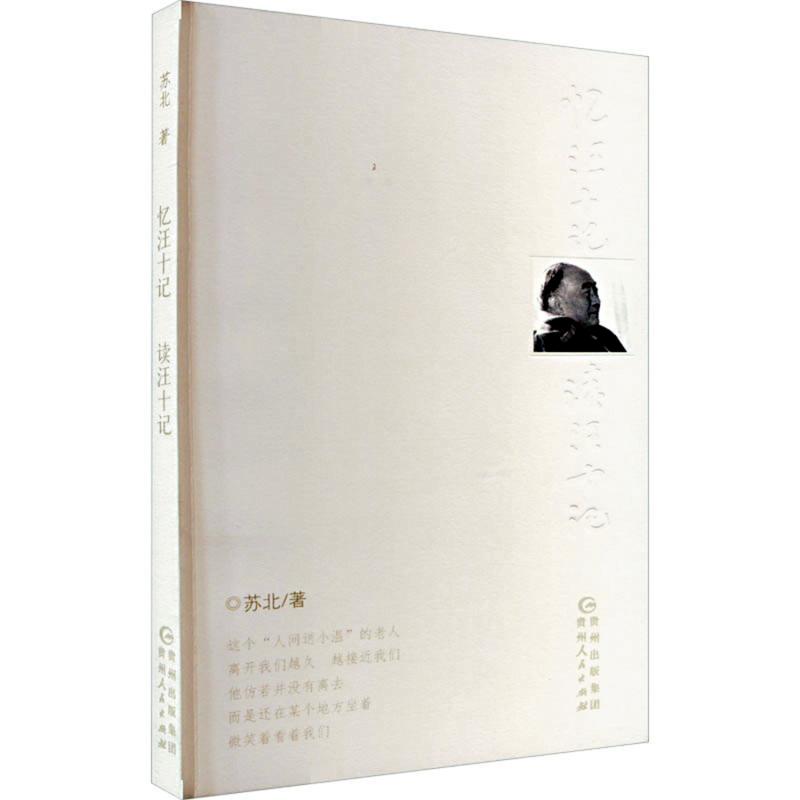
图:苏北散文集《忆汪十记 读汪十记》。
──读苏北散文集《忆汪十记 读汪十记》有感
二○二三年深秋的一个午间,合肥的黄山书会上,我参加完一个小型访谈活动,恰好遇见苏北先生。他依旧是方格衬衣(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件方格衬衣,好像每次是,又各不相同),戴着金属框架眼镜,儒雅地与一旁的人谈天。我赶忙从书堆上抄起一本先生的《忆汪十记 读汪十记》到收银区买单,而后飞奔到先生跟前,让他给我签了名。苏北先生墨宝了得,二王韵味足,只可惜这次用的是水笔,他说,明天才是我的签售主场。而我,下午就要赶回亳州去。
苏北师承汪曾祺,从手抄四大本汪曾祺的著作邮寄给先生始,到培训班上结识先生,一通畅聊,就成了汪曾祺先生的座上宾,何其幸运,也何等令人羨慕。《忆汪十记 读汪十记》中,有一篇《行走笔记》,讲的就是他专程赶到汪曾祺生活的故乡去,从扬州、江都县、高邮县、兴化市,到宝应县、淮安市、洪泽县,后来,这次近乎“朝圣之旅”,让文坛诞生了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他的笔名就叫“苏北”。
苏北早年以汪曾祺研究为主,出了多本汪曾祺研究著作,不说是“汪学”研究集大成者,也至少也是国内知名的汪曾祺研究专家。《忆汪十记 读汪十记》是写得最生动活泼的一本,由苏北早年的一些书籍精编成册,他从颇为家常的角度回忆自己与汪曾祺的交往经历,以及深学汪曾祺为人为文的相关往事,有些回忆录的意思,却又不全是,总能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苏北从汪曾祺的一个眼神写起,忆起自己与汪曾祺的初识、再识、相处、分别,汪曾祺与黄裳、沈从文、林斤澜、黄永玉等诸先生的往来趣事,不管是躬亲还是别人转述,苏北的笔触都有极强的在场感,感觉他是一个托腮听先生讲课的学生,用全部的精力凝心聚神地瞩目、聆听、感悟一个人。
而后十记,是苏北读汪曾祺名篇的感受,《大淖记事》《晚饭花集》《受戒》等,与别的文学评论家不同,苏北往往是第一现场感知,加上自己的回忆穿插和第一手资料掌握,读到令人击节拍案,手不释卷。
不得不说,苏北是得了汪曾祺真传的。我曾读过苏北发在《人民文学》《散文》《光明日报》《文学报》等诸多文学期刊上的文章,恬淡得像是被名厨吊了很久的一锅清汤,乍一看简淨至极,仔细一品方知后味是波涛汹涌、江海激荡。
苏北有一斋号:慕汪斋。一段师徒情倾注一种书卷气,两代文人缘烙下一根接力棒。
一位学生对一位先生的追随可以长达多久?也许是三五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一辈子!显然,苏北是后者。苏北对汪曾祺的追随,从文字的风格上可以看出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试举一例——
汪曾祺的《隆中游记》有段落:
往桑植,途经襄樊,勾留一日,少不得到隆中去看看。
诸葛亮选的(也许是他的父亲诸葛玄选的)这块地方很好,在一个山窝窝里,三面环山,背风而向阳。岗上高爽,可以结庐居住;山下有田,可以躬耕。草庐在哪里?半山有一砖亭,颜曰“草庐旧址”,但是究竟是不是这里,谁也说不清。
苏北的《行走笔记》有段落:
十二点二十分钟上车,车开了一段,到了洪泽湖大埂。洪泽湖真大,车在湖埂上整整开了半个小时,才另择路。湖里有许多船,小如蝌蚪。湖若是张白纸,船便是几滴墨汁。
细细一品,简直毫无违和感,即便混杂一处,外行也是看不出来的。当然了,评价一个作家的高明或成熟,单纯只是像某个前辈作家,这不是什么坏事,但也绝非是一件大好的事。苏北的文字是有着自己特色和魅力的。
若非要拿汪苏师徒来类比,我倒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较,汪曾祺的文字是老辣的温和,苏北则是温和的老辣,两者是有分别的。通读两位先生文字多年,我还有种感受是,汪曾祺的文字在烟火气之外多了一重幽冷的格调,苏北的文字是烟火气之中多了几许诙谐和俏皮。比如,苏北在《汉韩侯祠》一节中有如许句子:“韩信当兵多年,一直不被重用,只得逃走,幸好被萧何追回,有‘萧何月下追韩信’一说。可有谁追我呢?”最后一个问句,扭转乾坤,立马可爱奇崛了。
最喜看《忆汪十记 读汪十记》中苏北到汪曾祺家做客,师父拿出五粮液给苏北喝,自己肝不好,也要拿葡萄酒来陪,菜也只吃极少的几口,足见情谊之深,款款端端涌动在笔尖,又在笔外流淌。
汪曾祺离开我们二十六个春秋了。
汪曾祺离开我们十年的二○○七年,苏北凭借《关于汪曾祺的几个片段》荣获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