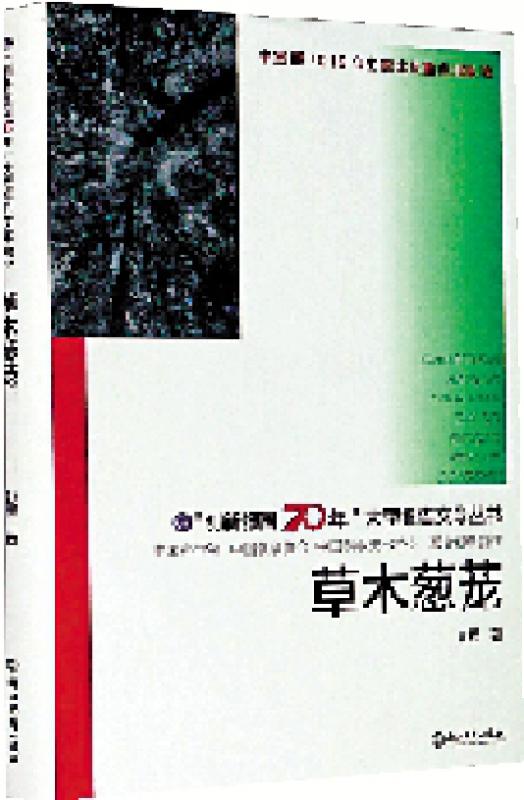
图:《草木葱茏》用翔实的数据、生动的故事,还原近百年来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轨迹。
作为中国近代植物学先驱、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胡先骕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与同时代的青年学者们一道,栉风沐雨、宵衣旰食,跋涉劳作於山野之间,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最终编纂了多达一百二十六册的《中国植物志》,填补了中国科学领域的空白。这弥足珍贵的成果,像是一封永恒的“绿色”情书,深情地写在广袤的国土之上,其背后是一代学者拳拳报国的赤子情怀,令人肃然起敬。而胡先骕先生二十四岁时写下的诗句“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正是这一群体精神高地的真实写照,给当代青年以深刻的人生启迪。
长篇报告文学《草木葱茏》(浙江教育出版社,二○二○年十二月),用翔实的数据、生动的故事,还原了近百年来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轨迹。更为重要的是,书中不但将植物分类学“是什麼”通俗易懂地进行了阐释,还深刻地揭示出植物分类学对於国家科学研究和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并由“为什麼”出发,生动再现为祖国创建这门学科的“时代先行者”鲜为人知的故事,耐人寻味。以“史”为本,以“志”为轴,以“情”为线,搭建了自然、历史和人组成的三维空间,《草木葱茏》的厚重也正在於此。
植物分类学看似比较学术、有一定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但实际上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就拿香港来说,媒体报道中经常提及的“香港市花洋紫荆”,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香港市花的真名叫“艳紫荆”,和紫荆花并不一样。这运用了植物分类学的基本知识:“艳紫荆”是红花羊蹄甲和宫粉羊蹄甲的杂交种,这两种亲本都在豆科的“羊蹄甲属”,与紫荆花(豆科紫荆属)算是远亲。我们由身边的一草一木,进而关心它的名称、类别与特性,不论自觉与否,我们实际上已经同植物分类学发生了交集与关联。
在《草木葱茏》的作者彭程看来,植物分类学的意义又不止於此:谁掌握了它,谁就打开了与世界生物学对话的那扇门,这对於一个国家来说,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尤其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複杂多变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繁茂的植物资源,创建并发展植物分类学,才能对国土和生态有更科学的保护。
报效祖国 献身科研
《草木葱茏》的可读性,首先在於真实。它没有讳言中国在这个学科上起步晚的事实,特别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科学教育落后,知识和学理形态的植物研究一片空白,直到上世纪初,才由志在科技救国的青年才俊从国外引入。彼时,中国的植物研究从标本採集到整理鉴定,都由外国人来做,这让胡先骕、锺观光、刘慎谔等一批青年学者深感不甘,他们自己动手、创造条件,节衣缩食购买植物标本和专业图书,千辛万苦建立起我国第一个植物标本室,为国家和民族争了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可以在国外享受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优渥的生活,但为了报效祖国,他们毅然回国,加入植物研究的行列。
“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书中对这句诗的反覆吟诵,引领读者更加深刻地领悟植物研究者身上所蕴含的精神品质,有效地强化了作品的深度和艺术张力,令人过目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