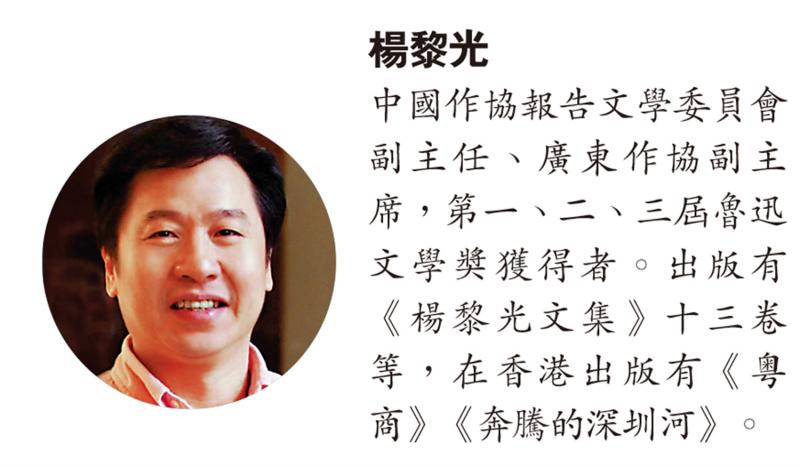
图:杨黎光─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广东作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十三卷等,在香港出版有《粤商》《奔腾的深圳河》。
编者按
香港与深圳一衣带水,文脉相连,两地文化交流合作活跃,港深文学间的联系和互动愈趋紧密。一场场文化上的双向奔赴、精神上的同频共振正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今期“大公园”邀请四位深圳作家书写他们眼中的香港,讲述他们的深港双城故事。
第一次眺望香港是一九八六年,那年我来深圳文锦渡海关采访,在海关朋友的陪同下,走到文锦渡桥头朝南望去,一辆接着一辆高大的货柜车排着长龙,来往在文锦渡桥上,十多米开外,那就是香港。
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再次来深圳采访,当年文锦渡海关的朋友调到罗湖海关工作,他领着我来到罗湖桥头,看着那如过江之鲫的人流穿行于罗湖桥上,每一位进出香港的人,都行色匆匆的,这是我第二次看香港。
也是这次在罗湖桥头,我的朋友对我说:“小杨,来深圳工作吧,深圳需要像你这样的人。”那时,我还叫小杨。
一九九二年元月我就来到了深圳,在一家报社工作。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第一次去香港,当时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无数抬头落帽的摩天大楼,和就是到了午夜,街头也是摩肩接踵的人群。
一九九六年底,报社建了一栋公寓,我分在二十三楼,书房的窗外视野所及就是一条如练的深圳河,而河的南岸就是香港,我几乎天天都在看香港。
二○一三年我搬到南山居住,书房窗外的远处就是深圳湾,对岸仍然是香港。
二○二二年,我来深圳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小杨已经变成了老杨。老杨就想为深圳写一本书,以表达我对这个城市的感情。从何着笔,望着窗外深思,眼睛里出现的仍然是那一条如练的深圳河。
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念头,三十年来,无论在深圳与香港,首先见到的都是这条河,因为它连接着深圳与香港。如是,我的书就着笔于这条河。
其实连接深圳与香港的不仅是山水,更重要的是血脉,因为深港同根。
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被今天的人们渐渐地淡忘了。
二○○三年初的一天,有一位名叫黄虎的香港人,在西贡企岭下海的一个无名海滩钓鱼时,偶然发现沙滩上的几块石头有点奇特。黄先生是学考古的,他立即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大学学弟、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吴伟鸿鉴别。
很快,香港考古学会与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组成了联合考古队,于二○○四年底对无名海滩上的一个叫黄地垌的缓坡进行考古发掘,竟然发现,这儿是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制造场。
通过光释光测年技术测定,黄地垌出土的第一层石器,距今竟然有三万五千年至三万九千年,也就是说,我们的先人,至少在距今三万多年前就已经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的“黄地垌遗址”的发现,一举把深港地区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人类活动史,向前推进了三万多年。
在史前的漫漫长夜里,这群远古先民究竟在深港地区经历了怎样漫长而剧烈的沧桑变迁?
“黄地垌遗址”所在的香港西贡企岭下海,位于大鹏湾西岸。
大鹏湾是个U型海湾,东岸是深圳的大鹏半岛,西岸是香港的九龙半岛,在台风频繁造访的南海之畔,这类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风平浪静的亚热带浅海湾,既便于日常渔猎,也利于躲避台风的侵袭,自然成了与大自然对抗时,手无寸铁远古先民的伊甸园。
而在大鹏湾东岸北岸的深圳,先后发现了咸头岭、大梅沙、小梅沙、上洞、大黄沙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大鹏湾东岸发现的“咸头岭遗址”。
这些考古发现,至少在三万年前,深港的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根。
而连接我们深圳与香港的深圳河,其实它的历史并不久远,在古南海水海侵海退的历史长河里,至少晚至北宋末年,今天深圳河干流的罗湖、福田和香港新界,大片低地仍在海水之下,或者是潮来潮往的浅海滩涂。至南宋、元两代,连年战乱引致的南下移民蜂拥而来,大规模束塘筑田之下,深圳河岸线急剧收缩。明清时期,海退加速,吸引了更多拓荒者进入,形成了一个人进水退的正循环。于是,时间和空间联手,自然和人工合力,终于将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深圳河推进了蜿蜒史册。
然后,它缓缓地经过千年的流淌,这条名不见经传的河流,却被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弱肉强食的历史潮流无情地裹挟着,奔腾流进了惊涛拍岸的二十世纪,宿命般地成为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记录者。
于是,我所落笔的深圳河因连接着深圳与香港,写着写着,原来想写一本深圳历史的书,就变成了深港历史,它的首章即为“深港同根三万年”,它的书名也变成了《奔腾的深圳河:一条河,两座城,中国与世界的相遇》。因为,深港不仅山水相连,还血脉相通。
深圳河,既是一条自然存在的河流,河的两岸牵系着深圳和香港世代黎民百姓,见证着他们的悲欢离合;它更是一条历史的河流,今天缓缓地流进了深圳湾,汇进了“粤港澳大湾区”,深港以及珠三角的人民,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未来。
这就我一个作家所看到的深圳和香港,我的书也结束在一个未来的“湾区之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