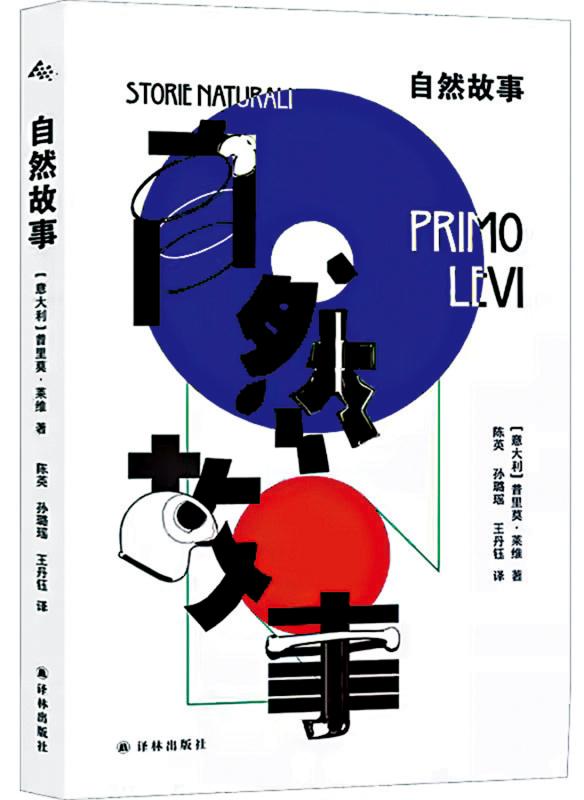
图:普里莫.莱维著《自然故事》。
科幻小说里面的内容,在它发表的年代里是不折不扣的“幻想”,多年后再读,那就不一定了,也许就是已经兑付了的预言,是业已降临人间的现实。意大利作家普里奥.莱维小说集《自然故事》里面的某些带有“技术”含量的篇章,以我一个文科生的认知,已觉得不算科幻了。比如《冰箱里的睡美人》里面一九五二年出生、一九七五年被用冬眠技术冷冻起来的睡美人,一百四十年在冬眠中,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小说发生的二一一五年,但是冷冻卵子或人体某器官的事情,我已听说过。《自然故事》这本小说集初版于一九六六年,那时候静电复印机已经用于办公领域,不过《划算买卖》里面的“覆製机”可不是在纸张上复印,它能覆製钻石、豌豆、蜘蛛,当然也有可能覆製人。这不由得让我想到3D打印技术和生物基因克隆技术。还有《颜值测量仪》中的这个仪器,我认为配上人工智能的人脸扫描仪完全可以给人的颜值打分了……总之,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小说里让人张大了嘴惊掉下巴的很多情节,今天已经是白云悠悠的生活日常了。
卡尔维诺在《初版编辑后记》里说,《自然故事》用十五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将我们带入一个由技术进步的狂潮推动的未来”,他还提醒:“但仅仅将这些作品归为科幻小说是不够的,因为故事中还包含讽刺和诗意……”我想卡尔维诺写下这些时,一定联系到莱维的人生经历──事实上,他的经历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莱维是作家,化学家,还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据说在他所乘的列车上,六百五十名意大利人中,仅有二十名幸存。一九八七年,莱维的人生句号又是自己画上的。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有了中译本,叙述他人生传奇的《普里莫.莱维传》有中文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翻看。在这个AI时代,我感兴趣的是《自然故事》中的《作诗机》一篇。
如小说题目所示,有人发明了可以作诗的机器,替诗人解决了无法按时完成订户订购诗歌之苦。而且诗人对它的依懒性越来越大,不过两年就有如胶似漆之感。小说里这位诗人说:“我拥有这台作诗机已经有两年了。我不能说已经完全接受它,但我已经离不开它了。这台机器多才多艺:分担了我作为诗人的大部分工作,除此之外还帮我记账,提醒我交稿日期,帮我写信。实际上,我已经教会了它如何写散文,它学得很不错。”记得我小时候曾梦想有一台写字机替我抄作业,其时打字机尚在人工打字阶段,后来有了电脑,语音识别技术,如今的AI真的可以帮我们完成作业了。这可不得了,我看复旦、交大两所高校赶紧出台规范,不接受纯粹AI写出来的论文,事关学术规范,兹事体大。不过,诗人们向来浪漫有余,有个中国诗歌网宣布,它们已接入DeepSeek,投稿自动生成AI点评。随后,还将自动生成绘画作品,自动生成歌曲。哈哈,什么都有了,打通了。
莱维的《作诗机》时代,电脑还未走入日常生活,互联网更属科幻,语料库呀,大模型啊,更是闻说未闻。那是一个机械时代,作诗机还是一个可听话的打字机形态,不过,作家的想像力还是可以的,这台机器使用时,需要诗人输入主题,调好风格调整器,主题、语体、韵律(行数、音节)、限定诗歌年代,这些搞定后就等着机器在打印纸上吐出诗行了。诗人对于机器写出来的诗评价是:“天才之作当然说不上,但有商业价值,应付实际需要已经绰绰有余了。”哎哟,我一愣:这不就是DeepSeek吗?
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蛇年春节假期里,我的朋友圈共同的主题就是那个蓝色小鲸鱼标志的DeepSeek,它代替了烟花爆竹,扑克麻将,春晚抖音,走亲访友,成为人们娱乐新宠。说“娱乐”,是大家多处在一个玩的状态。这就不得了,据说有人在家抱着个手机有说有笑,几天都不抬头看老婆一眼;自恋的作家,不断地让DeepSeek评价他的作品,一遍“不准确”就两遍三遍,他兴奋地把结论发到朋友圈里,洋洋得意地告诉大家这是高科技的认同。人们关于DeepSeek的体验、议论、猜想、畅想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有人说将来DeepSeek开出的药方,比著名医生开得都准确,因为它存储了不计其数的病例。翻译家说,这东西是重要帮手,并拿它找出了很多前辈翻译家译文中的问题。《新民周刊》记者以迎接科学的春天的口脗宣布:“DeepSeek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算力规模,实现足以匹敌美国顶尖AI模型的效果,震撼整个市场。”“一石激起千重浪。DeepSeek让一众海外AI巨头集体‘破防’。”这些话如听梦呓,但有一点我感受到了:DeepSeek,火了,不是一般的火。
那么,文科生还有出路吗,尤其是写作者。莱维小说里诗人买一台作诗机价格不菲,DeepSeek却是免费下载,手机可用,随时随地。作家、诗人们还能有饭碗吗?随兴奋而至的是焦虑,高科技带来的焦虑,也把每个人弄得不得不作深思状。
作者简介:周立民,现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另一个巴金》《巴金画传》《巴金〈随想录〉论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