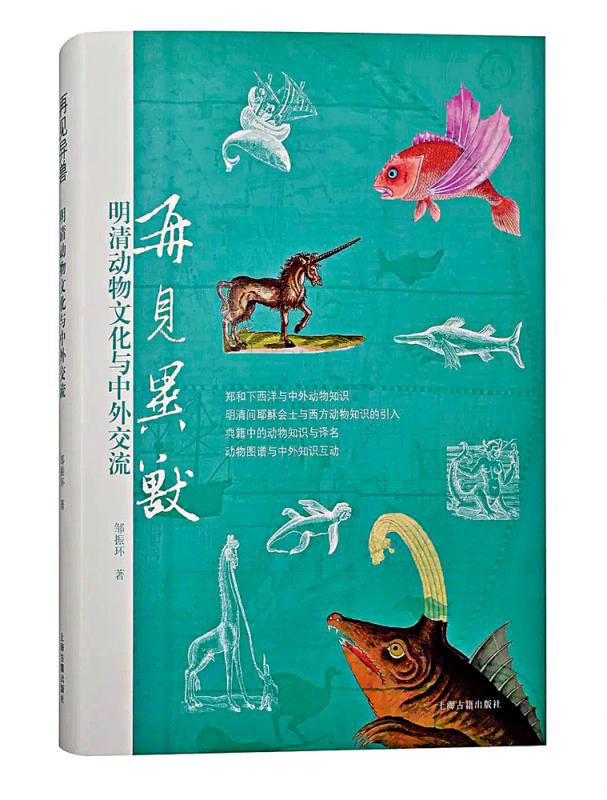
图:邹振环著《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二二年。
《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邹振环的新著。本书围绕一四○五年郑和下西洋至十八世纪干隆时期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文献中或国人想像里的珍禽异兽,展开了一场专业严谨而又妙趣横生的动物之旅。
本书除导论和全书结语外,共分四编十一章,前两编主要分析了郑和下西洋、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及其编译的地理学图书对于动物知识建构的影响,后两编则关注典籍中的动物知识与译名,以及动物谱图与中外知识互动。应该说,这是一本专业而有趣的书。
珍禽异兽
说它专业,是因为本书作为动物史和动物文化的学术研究,建立在深厚的文献基础之上,特别是作者运用了明清间《坤舆万国全图》《职外方纪》《坤舆图说》《狮子说》等汉文西书,以及《澳门纪略》《兽谱》《海错图》等明清动物文献,还有晚清出洋人士的记载等,着意勾陈动物知识谱系及其建构,从中西动物交流中发掘不同文化系统接触时的互动策略及新知识的生成。
说它有趣,是因为对于作者在书中介绍的内容,或许正好处于不少读者的知识盲区。比如,长颈鹿为何被认作瑞兽“麒麟”,海豚、犀牛、鬣狗又曾分别对应着“仁鱼”、“鼻角”、“意夜纳”等不明觉厉的名称,大象在东亚文化中具有何种地位,等等。在本书勾勒的神奇动物世界中游览,颇有近来网上流行的“热门生物鉴定”视频即视感。
麒麟来了
对于麒麟故事的分析,是本书的重头戏之一。由此也可见全书寄意所在。麒麟本是中国古人幻想出来的一种独角神兽,被尊为“仁兽”“瑞兽”,并赋予其“兽之圣者”的美誉。麒麟现身被认为盛世降临的标志。民间也有麒麟送子、镇宅麒麟等说法。不过,谁也没见过这种神兽。直到长颈鹿出现,一直是个传说的麒麟才借鹿还魂般有了“真身”。
关于长颈鹿的记载,最早可能出自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书中说非洲有一种异兽,身高丈馀,颈长九尺。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则把这种“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的动物称为“徂蜡”。不过,把这种异兽和麒麟联系起来,源于郑和下西洋。永和十二年(一四一四年)榜葛剌国(今孟加拉)进贡了一头长颈鹿,引发朝野轰动。此后郑和的几次下西洋活动,都肩负着督促“麒麟贡”的使命。如果沿途各国无意上贡长颈鹿,郑和团队便自行购买,七次“麒麟贡”中目前可考的至少有两次的长颈鹿是买的。由此可见,麒麟贡的礼仪功能远大于经济功能。
郑和及其随员或朝臣将其名“祖剌法”译作“麒麟”,被作者认为是“聪明的译法”,因为“麒麟”发音和索马里语“徂蜡”接近,更重要的是把这种新动物和祥瑞之兆联系了起来。“这一动物译名可以向世人表示因为大明上有仁君,才有此瑞兽的到来。”明成祖果然十分高兴,令画师作麒麟图,传赐大臣。大臣们也纷纷献上“麒麟颂”,这些诗文汇编起来竟有十六册之厚。
而据见过宫中画师所作麒麟写真的人记载,“全身似鹿,但颈特长,可三四尺耳。所谓麕身、牛尾、马蹄者近之”,并特意说,和一般画中想像的“麒麟”模样“迥不类也”。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长颈鹿化身“麒麟”是一次有意的误读,用书中的话说,是“物灵政治”的需要,目的是确立和展示以明朝为中心的中华朝贡体系。如史学家何芳川所指出的,长颈鹿的进献,已经脱离了它本身物的意义,成为一种精神的东西,它象征着一个理想的实现、一种境界的达到、一项功业的满足。当长颈鹿成为“活麒麟”,它就变成了一种外交符号或润滑剂,亚非国家借此可以寻找彼此共同的利益和文化上的相互契合点。
动物知识
武侠小说里常有“隔山打牛”的描写,在文化交流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书中讲到,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一度把佛教作为自己的主要攻击目标,使用的方法是抹杀“贡狮”的历史。狮子不是中国本土的动物,但很早就从西域输入过。而且,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流行,狮文化越来越深入国人生活。狮子和佛有了某种文化关联,比如所谓“佛门狮子吼”。然而,一六三六年抵华,曾在澳门大三巴教堂附近的圣保禄学院学习汉语的利类思在其编译的《狮子说》中却认为,一六七八年葡萄牙国特使白垒拉向康熙皇帝献狮,才开启了活狮入华。书中这样说道:“狮子至中国,或由陆路,或由水路。由陆路势所不能。盖利未亚洲係狮子生产之地,陆路距中国四万馀里,……何由得进狮子来中国。”他的结论是,“属国所进者,特狮皮而已”。利未亚,即非洲。书中辨析,这种说法和史实不符。从文献来看,长安城奇华宫附近的兽园就养着狮子。而郑和下西洋后,很多贡狮“假道满剌加,浮海至广东”,一度还形成了贡狮高潮,引起朝臣的劝谏。作者认为,利类思长期在华传教,到过北京、四川等地,应当见过各地的石狮雕刻,之所以要“重写”狮子进入中国的历史,目的是动摇狮子与佛教的联系,转而让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群众基础”的狮子与佛教脱鈎,为天主教背书。正如利类思在《狮子说》所说,“今述狮之像貌、形体及性情、力能,不徒以供观玩畅愉心意而已,要知天地间有造物大主化育万物、主宰安排,使物物各得其所,吾人当时时赞美感颂于无穷云”,一番话道出了这场“狮子争夺战”的真义所在,也让我们看到动物知识塑造中的文化碰撞。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前面提到的长颈鹿身上。南怀仁绘制《坤舆全图》时,特别改用“恶那西约”(Orasius)作为长颈鹿的音译。在他看来,明代文献把长颈鹿译作“麒麟”抹去了其异域痕迹,“甚至掩饰了这一动物的跨国性,不利于中国人对这一本土没有的新动物本身的生物学认知,更无助于域外动物知识在华的传送”。到了晚清,出洋使团在国外又见到了长颈鹿。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在伦敦“万兽园”看到了被他称为“支列胡”的长颈鹿,并认为,西人的万兽园虽然动物多,但都是“凡物”,“麟、凤必待圣人出”。他或许并不清楚,这“形似鹿”,“仰食树叶,不待企足”的怪兽,当年就曾被称作“麒麟”。后来,长颈鹿还曾被译作“鹿豹”。清末出国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日记中记录了参观“鹿豹”,并表示:“鹿之为鹿,必不得强名之以古代之麟”。
书中还介绍,“长颈鹿”这个名字早在一八四○年代已被使用,但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成为该动物正式中文名,此时距永乐十二年(一四一四年)的麒麟贡,已有五百多年了。这个过程充分反映了西方动物知识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调适,恰如作者所言,“沉淀在动物译名中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复杂变化,亦可见一部浓缩的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