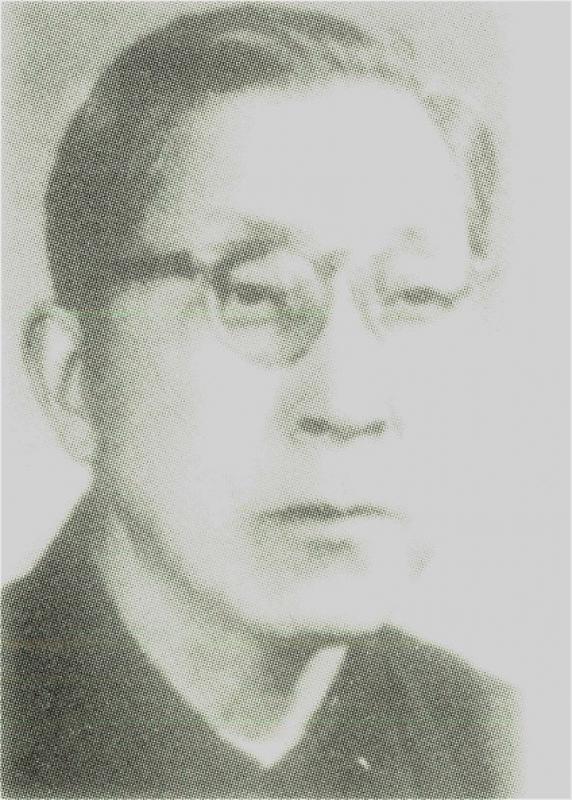
图:载於《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内的向达照片
月前在本栏介绍方豪《中西交通史》时,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方豪成书的差不多时期,著述中西交通史的历史学家,除了方豪之外,还有向达、张星烺等人。前者先后著有《中外交通小史》及《中西交通史》,后者则编著《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中外交通小史》是向达写於一九三○年的小书。顾名思义,这本交通小史篇幅很小,全书只有四万字左右,除绪论外,共分九章。但凡交通史,以至其他类别的史书,一般都以朝代或时代的名称劃分,例如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等等,作为书内的章目;然而,向达这本交通小史并非如此劃分。虽然并非按朝代劃分,但所用章目,倒也别出机杼,不但让读者一新耳目,更可从章目得知些许脉络。
书内章目 铺排特别
现将全书章目胪列如下,以便参阅:第一章“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第二章“中国与中亚”、第三章“中国与伊兰文化”、第四章“印度文化之东来”、第五章“中国与阿拉伯的交通”、第六章“中国文化之东被与南传”、第七章“景教与也里可温教”、第八章“中古时代到过中国的几位外国人”及第九章“明清之际之中西交通与西学”。
从上可见,这本小史的铺排颇为特别。向达此举,确有原因。他在书中正文之前所写的“作者赘言”说明,他有感於西方学者Henry Yule所编译而由Henri Cordier修订过有关中西交流的论著“收罗很详……考证也极详审……提纲挈领,颇为得要,於是据此写就这本小史。不过,Yule书内只提中西双方交通,但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的东被与南传,又没有提及中外交通在文化史上的收穫,更没有花篇幅谈及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通。”向达於是承接前书,稍予补述,写成此书。
另一方面,向达在书内的“绪论”指出,交通史在史学界可以有两种意思。其一,是专研交通制度本身,例如历代交通工具的变迁;其二,是研究一地与另一地在各时代的交往情况,而这就是两地之间文化交流史。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专研后者。换言之,这是一本中外文化交流小史。
向达亦在书内“绪论”说明,“我这部小史断限於张骞之通西域,止於乾隆之禁西教。”原因是“自汉武帝时代以后,中外交通方才有正确的史料可以遵循。至於止於乾隆之禁西教者,则因为之前的中外交通,大部分是雾裏看花,不甚明白,一直到乾隆时犹是如此。虽是朝代屡易,这一点观念却未变更。乾嘉以后,中外交通的形势起一空前的变革,外国正式以武力压迫到中国……”。向达随后解释,清代乾嘉之前,中外文化交流大都以中国为主体,乾嘉之后,中国处於被动。所以,他的小史专治以中国为主体的那段悠长交通史。
中国文化并不孤立
另一方面,向达亦在“绪论”指出,“中国的文化并不是孤立的。”那边厢,历代以来,四方民族很想与中国交往;这边厢,中国亦不断深入他国。历代例子,多不胜数;规模较大的计有:汉朝与匈奴及其他民族的互动、魏晋前后佛教自印度来华、唐朝文化东渡日本、南北朝及宋辽金元各代的异族被汉族同化,而汉族亦在同化过程中益见宏大。另一方面,“元明以后,中国同西洋又相接触……凡此皆可以见中国文化实无时无刻不与其他民族发生关係。”
要写一本目光广阔的交通史,作者不但必须深谙外文,懂得研究西方史籍,更须从西方的文献印证中西文化交流,务求做到中西两种角度兼备,避免单靠中国史籍了解中西交流。这一方面,由於向达学养极深,长期在欧洲钻研考究,绝对做到中西两面反覆印证。
首先,向达在书内第一章即“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内,以西方典籍印证中西交流。例如,他指出西方对中国这个远方国家有两种称呼。其一是Sinae或China,其字音是蜕变自汉字“秦国”一词的音译,必须注意,China一字如果以英语发音,则与“秦”字相距很远,如果以拉丁语或法语发音,则极为相近;至於Sinae一字,则较为明显可辨。时至今日,西方称汉学为Sinology,此词当然是从Sinae一字演变出来。
古希腊罗马时代对中国有另一种叫法,即Seres、Seras或Seria,意指中国的名产“丝”。由此可见,当时的西方是以“秦”或“丝”指称中国。然则,Sinae及China与Seres及Seria这两类称谓有什麼分别?向达在书内指出,Sinae及China大抵是指从北方陆路传去的中国,而Seres及Seria则指由南方海路传去的中国。
为了印证此等称谓,向达列举不少西方典籍,包括荷马及维吉尔的史诗、Horace、Ovid及Propertius的诗作,以及Strabo的《地理志》、Pliny的《自然历史》、Florus的《罗马史略》,而以上的文史典籍,都是专研希腊罗马文化的学者须予参阅的。
“葡萄”一词源自希腊
此外,向达亦在书内提述一些颇为有趣的知识。例如,我们日常生活所吃的葡萄,原来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词语,而这种既可酿酒亦可当作水果的植物,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有所见闻而带回中国。另一方面,向达引述二十世纪初英国Giles的说法,指出中国的傀儡戏、猜枚、刻漏、乐律等物事,以及海马葡萄镜等文物,皆由希腊传入。
上文提及的,尽载於书内第一章。至於其他八章,内容同样有趣易懂,只可惜本文篇幅有限,未能逐章载述。
《中外交通小史》初刊后翌年,亦即一九三一年,向达发行另一本同样讲述中西文化交通的史书,题为《中西交通史》。与只有四万字的《中外交通小史》相比,《中西交通史》篇幅虽然略大,但只有五万字左右,因此也只能视作一本小史。
我手执的版本,并非三一年的初版,而是一九五九年由台湾中华书局印行的台湾第一版。我是七五年在台北购得。最有趣者,是出版商基於政治原因,把作者姓名隐去。如果读者不知情由,根本猜不出,这就是向达的著作。
除“小引”及“叙论”外,全书分为十章,依次是:“中国民族西来说”、“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可孛罗诸人之东来”、“十五世纪以后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十八世纪之中国与欧洲”、“十三洋行”及“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大开”。
从书内的章目可见,向达先由概论讲起,然后大抵按照时序以若干特别课题论述。这种写法在某程度上与之前刊行的《中外交通小史》确有重叠,其中一个明显例子是《中西交通史》第三章“景教与也里可温教”与《中外交通小史》第七章“景教与也里可温教”章目相同。儘管如此,细观这两章的内容,重叠不多。简单来说,向达这两本书大可分开来读而各有进益。
《中西交通史》设计完备
另一方面,《中西交通史》在内容设计方面,比《中外交通小史》丰富。首先,书末设有“中西交通大事年表摘要”,作为附录;其次,书末备有中西文名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其三,书内载有十多幅插图。不过,向达所用的插图,全部採自其他书籍,绝非亲自绘画,而所有出处,已於“插图目录”内说明。其四,向达在每章尾部,不但备有参考书目,而且中西兼备。其五,每章“参考书”之后,亦设有“问题”一栏,就该章学习所得,提出若干较为简单的问题,俾使读者阅后温习。向达这种做法,想必是仿效西方带有教学功能的学术论著。
与前著《中外交通小史》不同,向达在《中西交通史》首章便处理中国民族是否来自西方的说法。“中国西来说”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及至向达成书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此说仍然方兴未艾。持此见者认为,中国民族源出巴比伦……中国百姓即巴比伦的巴克族。这一族人移居中国以后,对於本国的旧习以及传说,尚保存不少。如洪水传说的存留,神农即巴比伦的萨贡,仓颉即巴比伦的同基,黄帝即巴比伦的那洪特……中国同巴比伦的文字有很多相似的,必是出於一源的民族(见书内页三至四)。
向达所处的年代,碍於考古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尚处萌芽阶段,“西来说”根本很难有足够证据核实或否定。不过,向达指出:“要证明中国民族是否源自西方,一定要把地下的材料和纸上的文献,充分找出来,然后验之制度、文物、古代文字、声音、传说而皆合,稽之地下新出各种材料而不悖,方可作近似的决定。目前各种材料尚未完备,要决定中国民族的西来……为时尚早。此刻我们只好阙疑了。”从上述引文可见,向达的确是位“言必有证、理必有据”而恪守治学法则的学者,断不会基於民族情绪而妄下断语。
除了上述两本专书,向达还在不同年月写过很多关於中西交通(文化交流)的文章。单以一九五七年初刊而长达四十六、七万字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而言,就收集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计有:用作书名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关於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当中以首篇亦即用作书名的文章“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篇幅最长,并且最受重视。
此篇写於一九三三年的文章最受重视,主因是填补了学术界对於这个课题的不足。据向达亲述,前辈史家冯承钧(一八八七至一九四六)之前在《东方杂志》发表“唐代华北蕃胡考”虽然考证精确,但仅以蕃胡华化为限,而所取材料,只囿於《旧唐书》和《新唐书》两本正史,的确稍嫌不足。至於日本汉学家桑原隲藏(一八七一至一九三一)的“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一文,则以人为主,而文物及诸般方面,却无略述。向达有见及此,奋发为文,以唐朝由西域传入之文明而与首都长安有关者,逐一排列,依次叙述。他在文内逐一讨论“流寓长安之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长安打毬小考”、“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及“长安西域人之华化”。文末备有两个附录,其一是“柘枝舞小考”(“柘枝舞”属於教坊乐舞裏“健舞”的一种);其二是“盩厔大秦寺略记”(其时的盩厔,位於南山之阴,距离西安百多里)。
马球由波斯经西藏传入
这篇长文,记述範围广阔。例如他在“长安打毬小考”的一段裏,指出波罗毬(即Polo)是一种发源於波斯而西传至君士坦丁堡及东传至印度、西藏、中国以至高丽和日本的马上打毬之戏。唐人击毬,例以龟兹鼓乐助兴。向达甚至在该段文章力证,波罗毬在唐太宗年间才开始传入中国,而唐代以前,只有蹴鞠。唐代皇帝如玄宗、宣宗、僖宗等,均擅击毬,而僖宗除了精於击毬,亦擅蹴鞠鬥鸡。
这篇长文的确就唐代西域流入长安以及长安市内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提供丰富史料,其中更涉及绘画、舞蹈、音乐等艺术,足见向达史艺兼擅。其实,除了这篇长文,书内所收集的多篇文章,例如佛曲考、龟兹琵琶考、敦煌文学、宝卷文学、明清美术等,都是关乎艺术和文学的论著。如果学养不深,根本写不出前述文章。他的学养,绝对值得景仰。
根据统计,向达历年作品连译作约有一百,当中以单行本或编合成文集而坊间可以购得者,只佔四分之一左右。尚望有心人将其余专文汇集成书,俾能广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