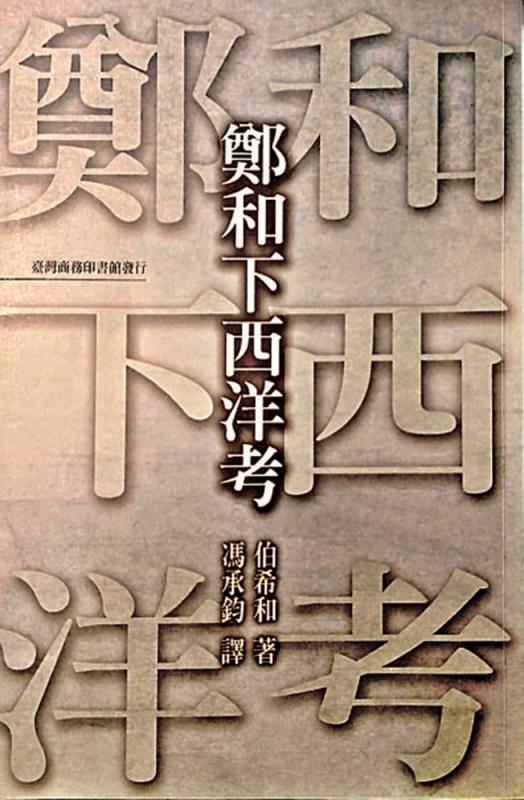
图: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二○○五年台湾版第三刷
之前在本栏论及岑仲勉编撰《突厥集史》的背景时,提到岑仲勉阅罢冯承钧翻译法国学者的《西突厥史料》,有感於该书所集史料,仅限於西突厥而缺少东突厥,於是奋力编集东突厥史,以补空白。
上述《西突厥史料》的译者冯承钧,是民国时代著名史地学家,尤专交通史,特别是中外交通史。其实,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中西交通史学研究的丰收期。当时出版的书籍,全属后辈学习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读物。当中计有:方豪的巨著《中西交通史》、向达所撰的《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张星烺的巨篇《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及冯承钧亲撰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及译自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等等。
南洋範围大语言多
关於方豪和向达的交通史论著,月前已於本栏先后述及。本文转为介绍冯承钧,但碍於篇幅,只可就论著、翻译及校註三大範畴各选其中最重要之一书,稍予介绍,即他亲著的《中国南洋交通史》、译自乃师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以及他校註明代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
冯承钧於一九三六年写成《中国南洋交通史》。据他亲述,执笔写这本书之前,内心充满矛盾。当时他虽然还没踏入“知天命”之年,但颇为害怕撰写大题目,更不喜欢他人邀约书写大题目,而中国南洋交通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大题目。他担心,纵使勉强写就,但内容难免疏漏,盖因“南洋範围广大,涉及语言甚多,非有鸿博学识不足办此。”(见书内“序例”)他虽然早已辑妥“南海地名”,但几年来还是不敢向人展示。即使儿子及朋友鼓励再三,仍犹豫不决,未敢动笔。适巧好友向达从英国寄赠一本Ferrand所写的《大食波斯突厥交涉及远东之舆记行传》,而此书大大帮助他考订地点,於是毅然执笔,希望本着“大辂始於椎轮”之意,为这方面的交通史稍尽绵力。
既然讲述南洋交通史,就必须先行界定“南洋”的範围。单以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的研究範围而言,南洋包含“东起吕宋,西达印度西岸”,但不包括阿拉伯海西岸各地,亦不包括安南、占城、缅甸、暹罗四国。关於此书的铺排,冯承钧先把全书分为上、下编。上编分十章叙述事迹,由第一章“汉代与南海之交通”起,至南北朝及唐宋元历代交通,当中亦依次以康泰、法显、常骏、贾耽等人作为章目主题。最后以“郑和之下西洋”作为上编终章。下编则以七章辑录史传舆记等典籍,计有:扶南(位於中南半岛)、真腊(即今柬埔寨)、阇婆(今爪哇)、三佛齐(今苏门塔腊)、南海群岛诸国、马来半岛诸国、印度沿海诸国等传。下编可视作上编之註释。
冯承钧在书内上编大抵指出:中国与南海之间的交通,究竟早至何时开始,实在难以稽考。不过,有史可征者,应始於汉朝,而有关活动可参阅《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西域天竺传”等;三国时代吴国孙权派兵出海宣扬国威时估计曾经到达琉球群岛(夷洲),而朱应与康泰曾经到达柬埔寨、暹罗(林阳国,今泰国)、缅甸沿岸,然后从恒河南下至锡兰(斯调洲,今斯里兰卡),惜康泰朱应所著遊记早已散佚,仅散见於《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古籍;东晋年间,僧人法显与几位同伴从长安出发,外遊十五年始归,据其亲述,最远所至之地,是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回归时经爪哇或苏门塔腊至广州。
法显之后,南北朝往来南海的僧人,可征者约有十名,包括觉贤、智严,而他们一般抵达印度甚至斯里兰卡,而部分僧侣亦行经阇婆,隋朝焬帝为求外国珍异之物,派兵去过台湾及越南,并差遣屯田主事常骏通往绝域(遥远之地),而他从广州出发,最远去到马来半岛之中的赤土国(据冯考证,往昔以为赤土位处暹罗境内,实误);唐朝贾耽曾从广州出发,经屯门(即香港屯门)经越南、新加坡、印度至西方,包括阿拉伯(阿刺壁)帝国、巴格达(缚达城)及弗利剌河(即幼发拉底河);宋元两代,海上交通繁忙,单从沿海所设的市舶司以通诸国货贸,便知一二。使臣商旅所到之处,包括南海诸地,例如真腊、渤泥(亦作勃泥、佛泥,即今婆罗洲)、爪哇、单马锡(今新加坡)、万年港(疑今文莱,而“文莱”一词,始见於《明史》)、北溜(即今马尔代夫,明代《瀛涯胜览》称之为“溜山国”)、天堂(或作天房国,即今麦加)等。
以上简述,皆引自冯书第一至九章。然而,全书最精要或最引起学子兴趣者,是第十章“郑和之下西洋”。此章篇幅不算很长,正文仅佔全书十二页。章内并非缕述郑和七次下西洋之行程及见闻,而重点在於订定正史之谬误。
力指乃师伯希和纰漏
一般学者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参阅《明史》“成祖本纪”及“卷三百四”“列传第一九二”之“郑和传”以及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然而,《明史》所记郑和之事,仅寥寥数百字,未及详实,而伯希和著书时,并未征引《明实录》及最新检得的相关碑石铭文。伯希和之书於一九三三年出版,随后一九三五年他於某学报发表“补考”,加引《明实录》的资料,但冯氏仍嫌不足,因此在第十章指出《明史》及伯希和书的疏漏。冯承钧作为徒弟,力指乃师伯希和之纰漏,实属学林佳话。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略举一二例。
郑和第一次奉命下西洋,据《明史》记载,是永乐三年六月;但冯承钧推敲,这只是奉旨的月份,而真正出发的月份,应在秋后。此外,《明史》只记郑和第一次自西洋回国是永乐五年九月;但《明实录》的记载,更为详尽,应是九月壬子(初二),并指郑和此行,最远至之地是印度西岸。另,郑和第五次奉命下西洋,是永乐十四年冬,但据南山寺碑所记,郑和统领舟师往西域的时间,是永乐十五年。其实,史书所记者,是奉敕年;碑文所记者,是出发年。此外,南山寺亦载述西域诸国,各献珍物,包括狮子、千里骆驼、驼鸡、金钱豹等。不过,关於郑和奉命及真正出发的时日,并非每次都有明确差别。例如,第六次下西洋,据《明史》“成祖本纪”所记,是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癸巳,而据南山寺碑所载,真正出发之日,即十九年春,与《明史》脗合。这是因为出海要配合季候,郑和必须赶及春季东北季候风止息之前出发,而不得耽误。
扼要而言,冯承钧在书内第十章引述其他史料,例如前述《明实录》及明朝文人祝允明所写的《前闻记》,矫正或补充乃师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内的疏漏及纰误。伯希和书写於一九三三年,而此书的冯承钧中译本刊於一九三六年。冯承钧无论在自己所著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十章内,抑或在他所译的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的“序”内,均举出例证,指明伯希和书内未善之处。
然而,冯承钧在中译本的“序”承认,儘管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外国有好几位学者曾研究郑和下西洋之事,但总嫌粗疏,未曾用心“寻究史源,勘对版本”,因此相对而言,伯希和的研究最为用心。可惜伯希和成书时,只参考《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及《西洋朝贡典录》的记载,但没有机会查核若干包含新证的典籍,例如收录於《国朝典故》的《瀛涯胜览》版本,及分别收录於《罗以智校本》、广州中山大学复刻“天一阁”本和《历代小史》本所收录的《星槎胜览》,以致有所遗漏。
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篇幅不算大,约有一百五十页。必须指出,这是一本考证书,不是缕述郑和七下西洋的事迹,而是将各本关於郑和下西洋的典籍考证校勘。为此,他在短短的引言之后,依次论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而以上四书,均属明朝永乐宣德年间出现的南海航行著作。至於《明史》内相关本纪和列传、《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明实录》等有关的典籍,则不在考证之列。
举例说,伯希和在“《瀛涯胜览》”一文,力证此书作者是亲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而不是张昇,盖因张只是修订者。此外,有些版本把马欢写成马观或马汝钦,实误;至於《星槎胜览》,伯希和指出,此书的版本问题,初则以为简单易索,但其实与《瀛涯胜览》一样繁複。扼要而言,此书有单卷本,也有四卷本,皆述及作者费信跟随郑和四下西洋而合共二十多年的经历。不过,此书始终未及《瀛涯胜览》详实,但两者应该併读,互补不足;至於“《西洋番国志》”一文,伯希和指出,此书是由南京人巩珍撰写。他曾随郑和出使西洋,共历二十多国。只可惜,此书散佚,正文未见,只可在《四库总目》看到浙江所进的《读书敏求记》内间接论说此书的文章。由於所载内容,谬误很多,以致“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西洋朝贡典录》”一文,是伯希和书着墨最多的一篇,几佔全书一半篇幅。《西洋朝贡典录》是一位名叫黄省会(字勉之)所著,估计初出时,只是一个手抄本,书成於一五二○年,而初刻本要待至一八○八年才出现。儘管流传版本很多,但从无人校勘,只有西方汉学家兑温达曾予註释及罗克希耳的英译本。伯希和有见及此,亲为该书按条校正。举例说,书内提及爪哇王的居所时,标明居所“周二百余步”,马欢《瀛涯胜览》则作“周围约有百余步”,而张昇版本的《星槎胜览》,却夸张地写成“方三百余里”。据伯希和推敲,张昇所言,当然无理,而马欢版本,似脱一个“二”或“三”字;至於实情是二百步抑或三百步,则难以决断。
儘管一如冯承钧所言,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确有不足,但始终很值得阅读汲取。
为马欢《瀛涯胜览》校注
冯承钧除撰书、翻译外,亦为交通史籍校注,当中最值得注意者,是为马欢《瀛涯胜览》校注。一九三四年,他为马欢书校注完毕,在书前亲撰长序。他在这篇长达十九页的序文,扼要述及郑和下西洋的情况。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率兵将二三万,“多赍金帛”,造大舶数十艘。单以第一次而言,共有六十二艘,第二次有四十八艘。
除此以外,冯承钧在序裏基於历史观及爱国心,指出若以世界航海家而言,郑和比狄加马及哥伦布等早了几十年,但西方史书只提及诸位西洋航海家而不言郑和,实在不公!
另一方面,历代以来,大家都对郑和的宗教信仰存疑。他明明是回教徒,父亲是去过麦加朝圣的信徒,为什麼后来归皈佛教,并有“三宝太监”的名号。据泉州回教先贤墓文所记,郑和在永乐十五年五月路经泉州时,曾在该处行香祈福。很多人认定郑和改宗佛教。不过,据冯承钧推定,郑和并没有放弃回教,皆因当时的中国回教徒,既可笃信回教,亦可兼奉佛教,这种“回佛兼笃”,於信仰上并无不悖。
下西洋为彰国威宣皇化
马欢在自己所撰的《瀛涯胜览》之内,除了一个短序之外,亲撰一首七言的“纪行诗”,以纪其盛。诗云:“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於今孰可伦……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由此可见,出海目的,是彰显国威,宣扬皇化,而携回的珍物,多不胜数,其间甚至把叛逆或不服皇令的土王押回京师。
单以马欢所参与的行程而言,他就二十个所到过的国家,逐一纪实。例如,他对满剌加(马六甲)国有如下记载:“自占城(即占婆国,今位於越南)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即新加坡海峡),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遂名五屿。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両,否则差人征伐……”
《瀛涯胜览》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典籍,犹幸此书很容易在坊间买到,喜欢交通史的学子,实应捧读。
冯承钧所著,所译,所校,当不止上述三款。平情而论,他对交通史的贡献,比他所尊敬的向达以及方豪等学者更大,主要是因为他为西方擅於交通史的汉学家与中国交通史家及一般学子建立了一条学术桥樑,透过他的论著及译著,我们了解很多关於西方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