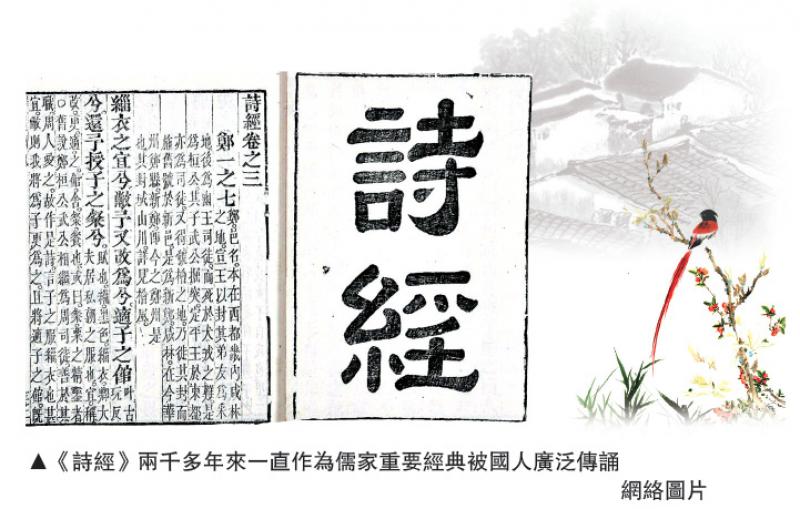
图:《诗经》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儒家重要经典被国人广泛传诵/网络图片
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观察,经由长期的积澱,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世界文学开始突进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新变,几个不同区域的古老民族几乎同时歌唱起来且形诸文字。希伯来文明出现了《旧约》诗篇,希腊孕育了《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印度衍生出《梨俱吠陀》,而中国则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诗经》。(《文学的历史动向》)闻先生高屋建瓴,扼要地指出了《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
《诗经》,原名《诗》,又称“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广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俗状况,是宗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自成书之日起就备受重视。春秋末期的孔子教育学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强调“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还特地告诫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子路》),都说明《诗经》在政治实践、外交斡旋、学术传承、移风易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降及西汉,《诗经》被立为官学,此后一直作为儒家重要经典被国人广泛传诵,至今不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先秦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滥觞与形塑期,《诗经》对此多有反映。要言之,约有以下三端:
其一,砥砺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主要体现在《诗经.大雅》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篇。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生民》写周部族始祖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帝尧命他管理农业,后稷“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天下得其利”(《史记.周本纪》)。《公刘》写公刘继续执行后稷“以农为本”的方针,“务耕种,行地宜”,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於是远近百姓皆来归附安居,周进一步兴起。《緜》写古公亶父为敌对势力所逼,不得不率族人由豳迁至岐,豳人感其仁爱,扶老携弱相从。在新的环境中,古公亶父与随迁百姓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不仅迅速安定下来,还完成了劃定土地疆界、设置百司宗庙、建立城郭等大事。《皇矣》、《大明》写周太王、王季、周文王三代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与商纣会战於朝歌郊外,“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终於推翻了殷商的残暴统治。从《生民》到《大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曲波澜壮阔的民族崛起史诗,诉说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的开拓进取精神。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愈是当国家民族身处困境之时,其光芒就愈发显现,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钱穆先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大,而至於其兴其亡,繫於苞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一苇何以障狂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笔者按:语出《郑风.风雨》),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可谓知言。
其二,崇德贵民的人本思想。王国维谈及殷、周之际中国政治、文化的变革时曾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裏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殷周制度论》)王氏所言甚判。周代统治者夺取天下后,并未被胜利衝昏头脑,他们不仅直面政治、经济的百废待兴,还试图解决下述疑问:商纣王不是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麼,那为何新兴的周能够取代绵延数百年的殷商?又是什麼使得“昊天大降丧於殷”,转而对周格外青睐的呢?经由一系列的严肃思考,周人得出了“天命靡常”(《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的逻辑推论。简言之,天命是不断变易的,它只会辅助有德的人;民心同样没有常主,只是怀念仁爱之主。基於此,周人不断告诫后代“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并构筑了一整套统治者须“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理论,这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古训。
其三,反躬自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天命靡常”的深刻反思相辅相成的,是诗经作者们浓重的忧患意识,他们深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蕩》)的道理,於是疾呼“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大雅.文王》),以期不忘初心、善始善终。他们认识到了“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是以要求上位者“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周颂.敬之》)在相传为周成王所作的《周颂.小毖》中,有这样的自警:“我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使以后不致再犯:不要招惹蜜蜂,它们虽小却能蜇伤人;开始相信那是小小的鹪鹩,转眼翻飞化为难驯地大鸟。”郑玄註释说:“毖,慎也。天下之事当慎其小,小时而不慎,后为祸大。”“惩前毖后”的成语即出於此。当这种意识内化为中华文化的基因,则如《唐风.蟋蟀》所说,“无已大康,职思其居”、“无已大康,职思其外”、“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即便在休閒娱乐之际,也保持着应有的节制与警惕。类似的还有《小雅.小旻》所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终身以此为準则,甚至在弥留之际还吟诵该段并对弟子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论语.泰伯》)。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此言得之。“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繫辞下》),这深沉的忧患意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
作为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处处可见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这些都成为后世诗歌主题、内容的不竭源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以下三方面。
乡国情怀。乡国情怀是对自己出生的土地不离不弃的眷恋和义不容辞的担当。每当乡邦遭受入侵或陷入困顿,志士仁人便挺身而出。“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鄘风.载驰》)许穆夫人听闻卫国被佔领,心急如焚,昼夜兼程奔赴国难,以其血泪写下这首《载驰》。当时的盟主齐桓公深受感染,派军队帮卫人戍守城邑,卫国民众也在许穆夫人爱国精神的鼓舞下重建家园。许穆夫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外敌入侵,家国危殆,铁血男儿互相感召、互相激励,“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诗经.无衣》)。全诗不断以重章叠句的手法增强语气,仅在相同句式中变换几个字样,展现了普通兵士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大无畏精神。对乡土的眷恋是爱国之情的细化,征夫虽深知“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小雅.出车》),然行役既久,不免怀念家乡,是以有“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豳风.东山》)之叹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之悲。自此以后,杀敌报国之情、羁旅行役之感、都邑乡关之思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的永恒母题。
第二,亲情、友情与爱情主题。“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邶风.凯风》),这是对母亲的歌颂。“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秦风.渭阳》),从此“渭阳”成为甥舅情谊的代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小雅.常棣》),这是对手足之情的肯定。“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小雅.伐木》),这是对纯真友情的嚮往。当然,《诗经》最打动人心的,还是那些爱情篇章,这裏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郑风.出其东门》)的专一,有“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鄘风.柏舟》)的勇敢,有“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邶风.击鼓》),更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召南.野有死麕》)的热烈,还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卫风.氓》)的决绝。是《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在此后的两千多年裏,亲情、友情与爱情主题被文人墨客反覆诉说,形成了异於西方的民族文学特色。
第三,怨刺讽喻主题。《诗经》的现实精神素来为人称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魏风.硕鼠》)分明是唐曹邺《官仓鼠》的远源,写下“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魏风.伐檀》)这与后世感叹“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陶者》)、“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的劳动人民同掬一把辛酸泪。“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小雅.大东》)的控诉无疑可视为左思《咏史诗》的先导,而“鸱枭鸱枭,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豳风.鸱枭》)则是《雉子斑》、《枯鱼过河泣》等动物讽喻诗的滥觞。
经由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的不断建构,自强不息的精神、崇德贵民思想、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鼎故革新,傲立於世界的东方。《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屈原、三曹父子、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黄遵宪等古典诗人,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仍有启示意义。
.李浩(作者单位:河北师範大学文学院)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河北省作协专业作家。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父亲,镜子和树》、《告密者》,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裏的父亲》,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莊重文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