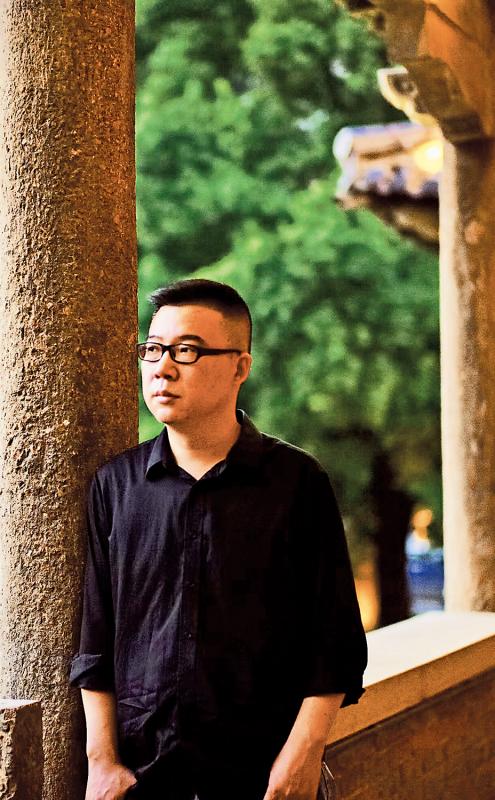
图:李修文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受访者供图
2024年5月,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推出他的长篇新作《猛虎下山》。在这部小说中,人变成了猛虎,再来反观世界,反观过去的自己。应对命运的遭际,猛兽与“我”,肝胆相照,抵达人生的辽阔之地,正如小说所说“肉骨凡胎,总要活在人间”。
这是时隔十五年,李修文再次推出长篇小说。他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作家往往不只是一个转述者和还原者,也是问题的处理者,要处理如何活着的话题。而万物格我,我也格万物,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在活里写,在写里活。写什么人,就去眼见为实;写什么地,就去安营扎寨。” \大公报记者 张帅武汉报道
《猛虎下山》以20世纪90年代末为背景,讲述镇虎山下炼钢厂改制转轨的故事。炼钢厂被收购后,小说主人公、被工友和老婆孩子看不起的中年炉前工刘丰收必然在下岗名单之上。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在厂区再现的下山猛虎叫停了厂里流窜的失业“老虎”。厂长决定重赏招募打虎勇士,报名者可免除下岗。
刘丰收主动请缨,借着酒劲独自上山“打虎”,结果酒醉一场只留满身伤痕,为了交差,他以一夜间长出的白发伪装成白虎毛发,谎称与吊睛白额虎搏斗了一场。刘丰收成了打虎英雄,厂长赋予他选人组建打虎队的权力。而随着时间流逝,“老虎”的存在逐渐受到质疑,刘丰收在对老虎的期盼中日渐疯魔,幻象丛生。被全厂围剿的下山猛虎,真相扑朔迷离。
隐喻真实时代事件
人与虎,猎物与狩猎者,双方从对峙到周旋再到互相吞噬。在绝对的困境当中,在绝对的孤独面前,人才是世间最大的魅。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称,《猛虎下山》里关于猛虎的巨大隐喻,让他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李安导演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用一个巨大的虚拟结构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时代事件,是它们的共同点。
李修文对大公报记者介绍,写《猛虎下山》这部长篇,陆续用了七八年时间。写作之前,他专门去了贵州的水城钢铁厂,这是一家曾为备战备荒而建设的工厂,过去轰隆作响的车间,现在变成荒草丛生的废墟。他跟钢铁厂的老工人喝酒聊天,酒醉之后,既听他们吹牛皮,也听他们讲述生命的辛酸苦乐。
到贵州水城钢铁厂采访,李修文每次都会带一把尺子,精确测量车床到车床之间的距离。之所以这么做,他说年轻时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有想像力的人,好像足不出户也可以靠想像力来写故事,但是每个作家的气质不同,对于他,仅凭想像带不来那种“飞蛾扑火”般的来自真实世界的写作驱动力。
顾随先生说,陶渊明之好,好就好在“身经”,意即能自己下手,就绝不旁观。李修文要求自己的创作就是“身经”,拿出力气来,用自己的身体去经历,而不是隔岸观火,“在活里写,在写里活。写什么人,就去眼见为实;写什么地,就去安营扎寨。”
“对我来讲,最大的不安全感就是不能确信写作到底是否抵近真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足为道,但如果未能抵近真实,会让我特别沮丧。”李修文称,作家强调“身经”并不是矫情,而是能够让他站在“他们”中间写作,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并以心换心,达到某种“通感的看见”。
写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猛虎下山》着墨了诸多勾心斗角情节与争夺、暗算、谎言等各种人性中不堪的部分。作者之意并非否定看起来泥沙俱下甚至不洁的人,恰恰相反,他觉得人生如丛林,每一次“猛虎出没”都是人生的挑战,那些有些疯狂的不洁之人,因为要活着,反而在试验人的边界,毕竟“肉骨凡胎,总要活在人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刘丰收的故事,无非是以万物为猛虎,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最让人触动的是一种生存的徒劳,许多对生命的热情都循环往复,最终又归于竹篮打水。但同时,无论是多么徒劳,它都构成生存于世的主体,面对每一场具体的战斗所付出的心力,以及在其中所受的损耗,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独特的存在。”在李修文看来,每个人都有必须面对的命运,它来了,你就走不掉,必须面对。而为了活着,猛兽与“我”,肝胆相照,共同抵达人生的辽阔之地。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刘丰收”,在采访中眼见所得的感受,给了李修文强大的叙述动力。他去过许多荒废的工厂,这些工厂跟内地其他地方反复经历的过程差不多,今天改制成这样,明天改制成那样,但事实上没有什么用,“最终,它们只能偃旗息鼓,而当年绝大部分的工人变成了‘失踪者’,在时代的烟尘笼罩下消失。”
李修文透露,很长时间里他曾对写作非常灰心,怀疑自己写不好眼前见到的生活,没有能力写出一个像孙少安、孙少平和福贵这样在文学中有名有姓的人,所以有很多年没有发表作品,但实际上还是一直在写作,包括这部《猛虎下山》,它的出发点还是想写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当我有机会听这些被时代烟尘笼罩的‘失踪者’像白发宫女一样讲述‘前朝旧事’,我还是能够跟他们深深地共情。跟他们深入到一起,你才知道,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各自携带着一部部史诗。”李修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