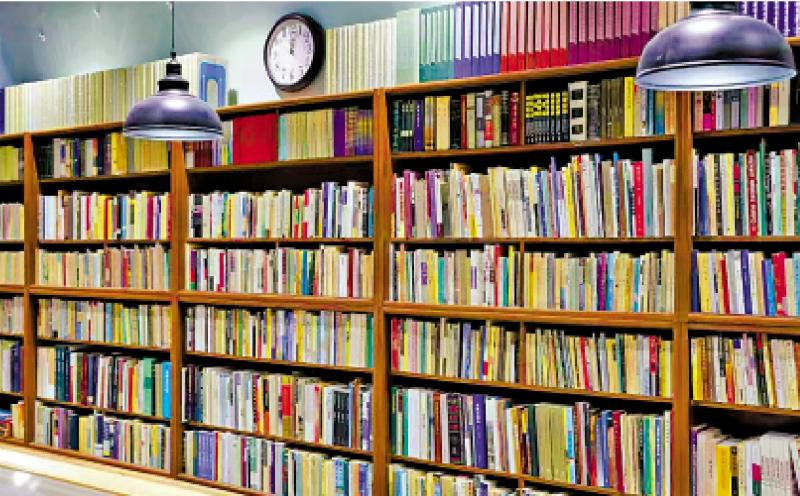
图:北京布衣书局内,抬眼可见书架上各类旧书。/中新社
本文的标题是从苏东坡先生那里借来的——在他写于1070年的《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一诗中,开篇即是这句“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当然,此诗是为劝解科考落榜的安惇秀才所写,他所说的“旧书”大抵是指为科考而必读的那些儒家经典,与我说的“旧书”原本不是一回事儿——故而,我才要申明这个题目是“借来”的。
我所说的“旧书”,原本也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早年印行之书,因年代久远而“旧”;二是指本人早年所读之书,因记忆久远而“旧”。前者是指一般意义之旧书,后者则指个人意义之旧书。鉴于我的读书阅历也有四五十年了,早年所读大半也可归入旧书的范畴,索性在本文这里就“一勺烩”了。
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相当多的爱书人偏爱旧书,且以淘旧书为乐事,以写旧书为专职,报刊杂志大多闢有“书话”专栏,一大批作家则以擅写“书话”而名闻于世,若郑西谛、梁实秋、林语堂、唐弢、知堂、阿英、黄裳等等。读旧书淘旧书写旧书,蔚然成风,由此构建起一个庞大而专业的“书虫群体”。于是,旧书的买卖也就成行成市了。
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旧书业兴盛的年代。当我初识文字想读书了,却偏偏遇到满世界无书可读的“非常十年”。书荒的日子很难熬,那种精神断粮所造成的心灵饥渴,与当年并行而至的肚子的饥渴,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可想而知,我小时候所能“偷食”到的书籍,只能是旧书了。
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文字书,是从家里小阁楼旧物堆里无意中翻出的一本又厚又破的旧书,封皮和封底都没有了,因此无法知道书名。单看内容,讲的是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正对小男孩的胃口。于是,我就开始如蚂蚁啃骨头一般读起这本旧书。此书是竖排繁体字,我起初大部分字都不认识,毕竟当时我还没上学,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但架不住那渴鹰饿虎一般的阅读欲望,不认识就瞎猜,一旦蒙对了就文通字顺,内情尽知;蒙错了就一遍遍再来,一遍遍试错,总有读通的时候。就这样,我硬是把这本厚达600多页的破书读完了。因为缺了几页结尾,所以对故事的结局我一直不晓得。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才知晓这本厚书名叫《吕梁英雄传》。记得我当时从报社图书室特意借来一册新版,从头到尾,重读一遍,却再也找不回当年躲在小阁楼上,废寝忘食地“啃食”那本旧书的快意和满足了。
由此发端,我的读书生涯便与旧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七十年代,彼时几乎所有早些年出版的书籍,只有极少量的“劫后馀灰”被保存下来,流落世间,顿成稀世珍品,被一双双饥渴的眼睛快速掠过。我算是幸运的,曾经遇到几个难得的机缘,得以多啃几口残篇剩卷。譬如,我父亲的一个师兄,在单位偶然接管了图书室的钥匙,而图书室的封条在风雨侵蚀中已形同虚设,这就使他有机会从封禁的书架上,“偷出”一些旧书拿给我父亲。这是我最早的一条旧书供应线。但好景不常,大概一年以后,那位师兄就被调走了,我这条线也就断供了。而恰在这时,我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供应线”——我有幸受所在小学主事者的委派,担任“红小兵广播站”的播音员,而跟我搭档的那位女同学,知道我喜欢看书却无来路,便悄悄从家里给我“偷运”旧书,一本看完,再换一本。就这样,这条“地下供应线”一直持续到我俩小学毕业——原来她的父亲与一所中专学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熟识,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让我得以借助她这条特殊渠道,读到不少“封禁”的小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缘于这段特殊的经历,那位慷慨相助的女同学在若干年后就成了我的妻子——评剧舞台上曾有一齣《花为媒》的喜剧,而在我的人生小径上却也演出了一折《书为媒》的“活剧”,我与旧书之因缘,何其深也!
自幼染上的旧书癖,想改掉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幸遇孙犁先生,九十年代又幸遇姜德明先生,这两位书话大家对我连续不断地予以加持,致使我对旧书的痴迷日益加深,渐成“书蠹痼疾”了。几十年间,我无论走到哪里,必去逛古旧书店,还常去地摊淘书。淘书品书,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旧书散发出的那种纸张发霉的味道,都令我陶然忘归,甘愿终日沉湎。十年前,在书友胡小跃的撺掇下,还编了一本小书,书名就叫《淘书.品书》。
由于早年所读,多有时限,匆匆读过,往往印象不深。因而,花甲以后退隐京华,时间宽裕了,我的阅读也开启了“怀旧”模式——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我着意于寻访早年曾经过眼的旧书,为的是重温旧时月色。譬如这本《豺狼的日子》,收纳同名小说和电影剧本,1979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我当年是从一个朋友手里“劫掠”而来,当晚读了一个通宵,翌日如约奉还——这哪里是读书啊,简直如同打仗抢占制高点——像这类当年粗读之书,如今,我都想慢慢地重读一下。故而,那天在潘家园偶见此书,登时喜出望外,当即收入囊中。还有一些旧书:若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科夫的《戏剧选》;若前苏联爱伦堡的《暴风雨》(上下册),尼.比留柯夫的《海鸥》;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都是五十年前的女同学“偷运”给我的。五十年后,她的父亲、我的岳父在临终之前一再叮嘱:“我的这些书,你们看着有用的,全都拿走吧……”
于是,我们把这些当年匆匆读过的旧书,精心地从老人的书架上挑选出来,安置到我家书房的“旧书专柜”里。时常翻阅,如同唤醒我们的青春梦影。是的,“旧书不厌百回读”,每回读罢,皆如聆听到深埋心底的“青春遗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