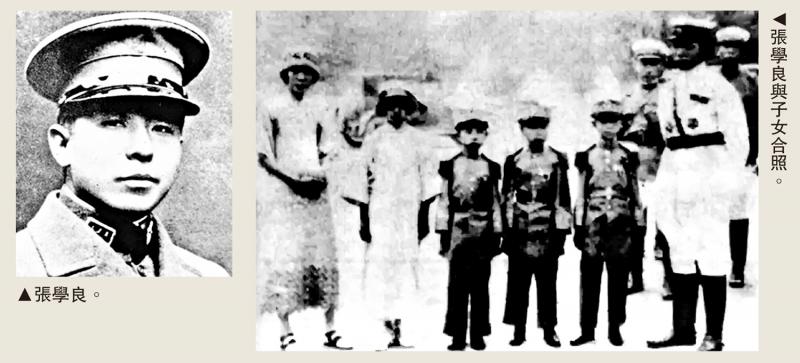
左图:张学良。右图:张学良与子女合照。
1928年,张学良因“皇姑屯事件”与日本关东军结下“杀父之仇”,但是,极少有人知道张学良与日本关东军还曾有过一段“夺子之恨”。张学良第三子张闾琪被残酷夺去性命,当时才9岁。
1920年春天,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张作霖亲自为这个孙子取名为张闾琪。这个孩子不但深得祖父张作霖的青睐,同时也为张学良伉俪的至爱。他长得与张学良酷肖,清秀而斯文。
稚子病危 旧臣力荐日本医院
6岁时,张闾琪就熟读了《四书》,唐诗宋词也能琅琅上口。8岁习英文,过目不忘。受其父母的影响,对大帅府“定远斋”内的书画情有独钟。仿效明代画家徐渭《葡萄图》所绘的《墨葡萄卷》,其笔法娴熟已到几可乱真的地步……才气之高,连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自愧不如。
可好景不常,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1929年秋天,张闾琪忽然染上了重病。初时咳嗽,后来发热高烧到39度。多方调治,病情非但不见好转,接连月馀高烧不退,陷入了昏迷状态,这可急坏了张学良夫妇。沈阳城里的外国西医几乎都请到了,张学良唯独不请日本医师,因为父亲张作霖死于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
本来体质清瘦的闾琪,变得越加孱弱。当年12月初,张闾琪尚有咳嗽症状,而中医通过诊脉又不能正确诊断其咳嗽久治不癒的症结所在。于是有一位深得张学良信赖的奉系旧臣,极力主张送张闾琪到“仰德医院”去照肺部X光片。
“仰德医院”是日本医生开办的洋医院,院长名叫广野三田,东京早稻田大学医科毕业的高材生,来奉天行医后名气较大。于凤至听说要把张闾琪送到日本医院照X光,马上表示反对。张学良初时也心存疑虑,他虽对广野三田的医名素有耳闻,但广野毕竟是日本人。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之时,那位素与广野三田有私交的奉系旧将再次陈词,并为广野三田的医德和为人拍胸作保:“广野三田行医多年,医德民望甚高,肯定和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日本医生,相信他绝不会利用给孩子治病之机暗做什么不光彩之事。”张学良心存的一丝介意也消除了。
关东军布杀局 半世纪后真相大白
在上世纪20年代末,X光机在偌大的沈阳,只有广野三田的“仰德医院”独有。因是张学良的三子就诊,广野三田显得格外重视,当天上午除接待张学良三子之外,所有求诊人员均做了延期诊治的处理。整个胸透室只接待张闾琪一位患者。
上午9时,主治医生川岛治重和一位女护士(也是日本人)将张闾琪推进胸透室,并安排坐在X光机前,广野三田亲自在外间照料。就在马际宇医官和几位侍卫在胸透室外等候得心绪焦急之时,突然听到胸透室内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好像室内有颗定时炸弹猝然发生了爆炸,胸透室内响起一声尖厉的孩子哭叫。
马医官等人暗叫不好,撞开内室玻璃门扑进去时,惊愕地看见一个悽惨血腥的场面:烟雾弥漫之中,胸透机的主机玻璃板不知何因在闭门的一刹那发生了爆炸。张闾琪此时已经扑倒在那架炸裂的胸透机前,脸部胸部均有淋漓的鲜血。再看那两个日本男女,仅仅是白大褂上沾些爆炸的粉尘罢了。
当天夜里,9岁的张闾琪便在帅府溘然而亡。
张学良派员去沈阳日本领事馆彻查“仰德医院”胸透机爆炸原因,日本领事馆和“仰德医院”均以种种借口推卸,迟迟不肯提交爆炸的原因报告。1989年,张学良在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恢复自由后,在台北会见了一位名叫池宫城晃的日本记者。这位《每日新闻》的著名摄影记者,把数十年来搜集的关东军秘密档案复印拿给张学良亲阅。通过这些绝密资料,张学良才惊愕地找到了历史的答案。
原来,1929年冬天,日本关东军获悉张学良将要送爱子前往“仰德医院”求医时,连夜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出面,以威胁利诱之手段,收买了广野三田,然后暗中布置日本特务在X光胸透机内密装炸弹,届时由特务幕后操纵引爆致死。可叹的是,张学良在解开这血腥之谜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
(摘编自《文史博览》文/窦应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