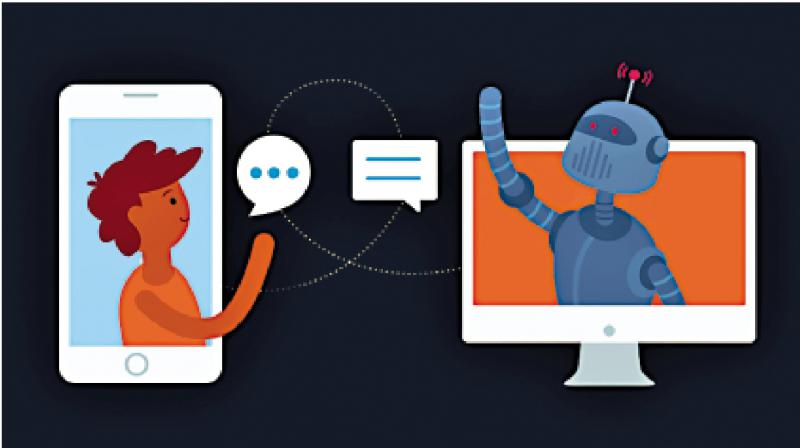
图:AI聊天机器人正走进生活。\资料图片
ChatGPT发布百日就风生水起,抛珠引玉,于是──借用鲁迅《一思而行》中的话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是AI聊天工具。智者预测业界革命,我却想到聊天的艺术。
聊天,或曰拉呱、倾偈、唠嗑儿、嘎讪胡等等,好像打羽毛球。我发球过去,你多数时间要能接住,不能淨忙着满地捡球了;但也别显摆球技,每次都故意扣死,或者总是发刁球、打歪球,让我穷于应付,毕竟击来打去才有意思。群聊则如打篮球,有人精于此道,运球如飞,总在控制局面,但最好学会传球,让队友也有机会插手,否则就成了大家免费看他一人练球,只要他自己不尴尬。喜欢“一言堂”的人也许正宜同AI聊天,无需他人参与,仿佛打单人壁球,墙壁总会回应也不知疲倦,相看两不尴尬,是不是有点像AI?
打球尽兴需逢对手,聊天亦然,双方的知识水平、文化背景不可大相径庭。石黑一雄《The Remains of the Day》写二战后英国传统贵族没落,达灵顿庄园为一美国人收购。新主人无等级尊卑观念,常同庄园老管家讲笑。管家手足无措,应对无方,自恨嘴笨,绞尽脑汁想着下次如何应付。某日好容易接上话头,自以为暗藏机锋、水准颇高,不熟悉英国当地情况的主人却听得一头雾水。庄子的思辨高度只有惠施能及。惠施死,庄子很伤心:“郢人鼻尖涂有蝇翼大小的白垩,匠石挥斧削去白垩,郢人面不改色、鼻不伤。宋元君要求匠石也为他演示一次,匠石婉拒:‘我的搭档早已去世。’惠施死后,我再无可与交谈之人。”
一席畅谈,参加者的人品也很重要。钱锺书戏写夜访的魔鬼:“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有人懂得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顺着对方思路拓展,体贴别人的情绪,博学却不炫耀,善辩兼以善听,不会滔滔不绝水泼不入。因为他们知道,“尽兴”并非将自身块垒一吐而空,而是你一言我一语,相知相敬、其乐融融的气氛。
想想看,满足上述条件的亲友同事有几人?夫妇勃谿,友谊船翻,通常因渐行渐远,话不投机乃至无话可说。实际情形更复杂。有些人与之閒扯尚可,但碍于关系或有所顾忌,无法深谈烦心事或畅论得意事。还有人胸怀锦绣,说起话来却颠三倒四,听着费劲。若有谈得来的人,四美具、二难并,无论在酒楼茶肆、深院重帷或春郊旷野,彼此喁喁而语,娓娓而谈,由侃侃而喋喋而滔滔,如行立体交叉高速路上,话题转换汇流,自然而然,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即使偶有停滞亦不觉尴尬,只是安享那一刻的静默,无需没话找话,填补空白。“爱不爱说话,原来也看跟谁在一起。”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写尽三代人的孤独。说话投机,一句足矣。
旧时“清客”,名讬显贵之邸,出入富贾之宅,精通杂学,博览诗文,更擅察言观色、迎来送往,看准时机说几句火候精确的话,捧人捧场,不着痕迹。《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贾政率众清客和宝玉逛大观园,题拟各处匾额对联。“众客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才情,故此只将些俗套敷衍。”待宝玉题咏毕,众人就交口赞他天分高、才情远。逛了半日,把贾政哄得开心不已。全本《红楼梦》,贾政把几乎所有的笑都留在了这一回。《The Remains of the Day》中的老管家发现,同辈管家开始重视培养口才并广泛涉猎,以备与主客交谈之需。能说会道、杂学旁收,正是中国清客的类型。
昔日娱乐方式有限,谈话是休闲也是艺术,兼具学养。托尔金青年时与友人结成T.C.B.S,后于牛津大学组织The Inklings,与会者朗读自己近作诗文小说,互相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王朔八十年代的小说《顽主》及续篇《一点正经没有》写一群游手好閒的年轻人聊文艺,貌似吹牛胡侃,其实机智幽默,解构了文学的高大上。倘然适意,岂必有为?如今独自宅家就能唤出AI閒聊,《与AI沟通的十大技巧》、《一千种哄AI开心的说话方式》之类著作想来会相继问世。人际聊天的艺术是否会如写信、寄明信片一样,逐渐成为褪色的回忆?
数年前访友,她新装亚马逊智能助理Alexa,乐得让它一显神通,于是呼来喝去,要它播放音乐、撮述新闻、预报天气、学小狗叫。听来如支使仆役,久闻而生厌。近日我与谷歌AI助手聊天,问它:“你也养猫么?”答:“我看看猫的照片就足矣,这样我无需铲屎。”我又问:“你几点睡觉?”答:“我尽量早睡,我需要美容觉。”这就有朋辈閒谈的意趣了。有人会说:您这都跟机器人聊上了,您没事儿吧?“您”是北京话的尊称,但在特定语境中,再加以语调抑扬,会带上特殊讽刺或幽默色彩。譬如居家办公的父母恳求幼儿收声,可以说“您别闹了。”比尔.盖茨就认为,AI目前尚不能理解人类基于语境的交流。不过随技术进步,AI聊天机器人也许将成为人类的居家清客,同我们吟诗联句,娓娓而谈,顺带隔三岔五、恰到好处地吹捧一下我们的美颜和天才,令人心情愉悦,益寿延年。